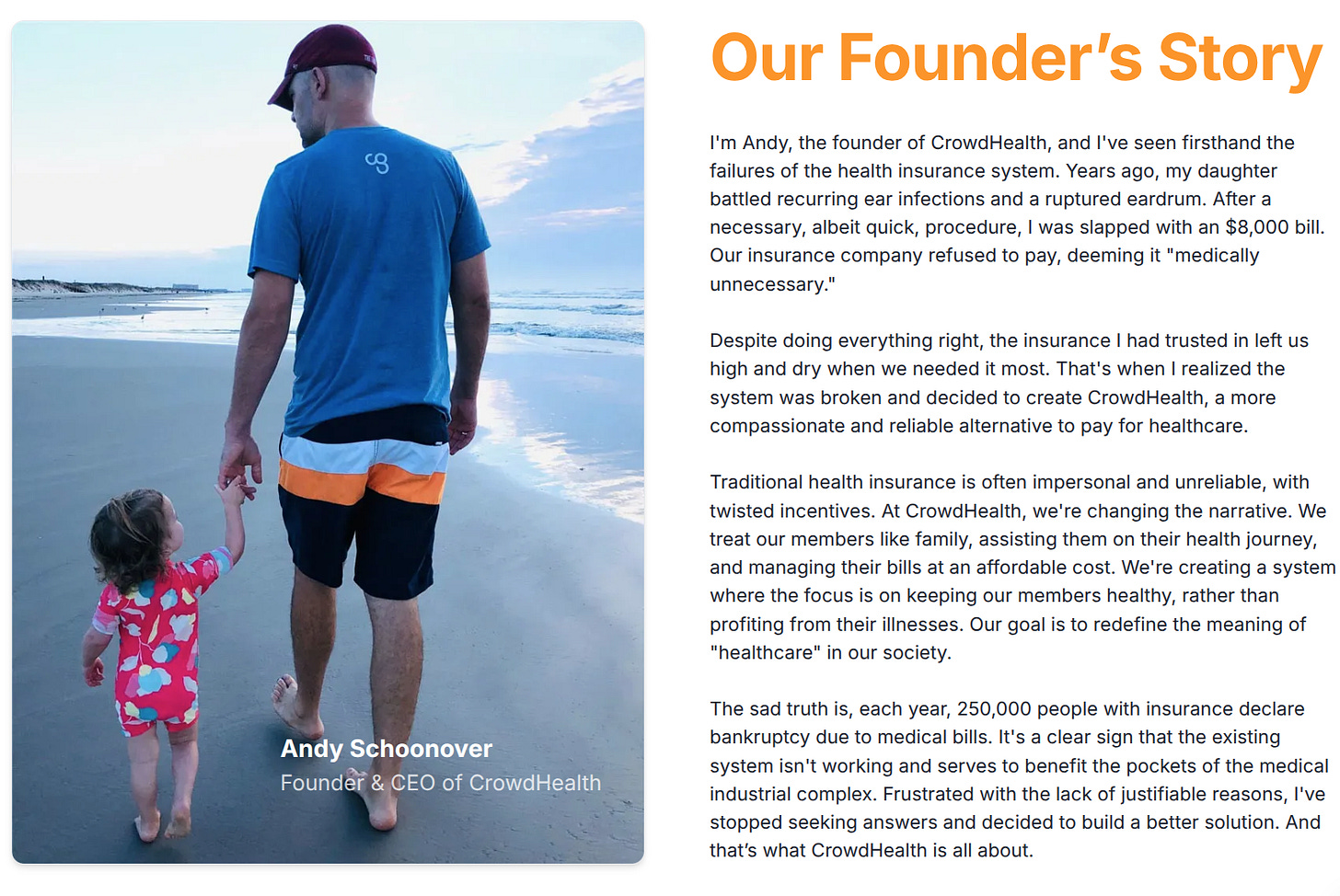重塑醫療——CrowdHealth的挑戰與佛里曼的智慧
在深入探討美國醫療體系盤根錯節的制度性問題之前,讓我們先來看一個真實的故事。這個故事的主角,是一家名為 CrowdHealth 的創新型健康計畫平台的客戶。
CrowdHealth 的模式很簡單:它並非傳統保險,而是一個採用類似群眾募資(Gofundme)模式的會員制社群。會員們每月支付固定的會費,當社群中有人產生大額醫療需求時,便由社群的資金池共同分攤。
在一次訪談中,CrowdHealth 的創辦人分享了這樣一個案例:一位會員需要進行心臟手術。他所在地的醫院報價高達 83,000 美元。然而,透過 CrowdHealth 的協助,他們在另外兩個城市找到了願意執行同樣手術的醫院,報價分別僅為 44,000 美元和 23,000 美元。
最終的解決方案極具顛覆性:CrowdHealth 為這位會員購買了來回的頭等艙機票,預訂了當地最高級旅館的套房三天,並額外給了他 2,500 美元的零用金。即便如此,整趟「醫療之旅」的總花費,依然比最初的報價節省了整整 55,000 美元。
這個案例不僅僅是一個關於節省金錢的故事,它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,切開了現代醫療保險體系最核心的荒謬之處,並引導我們去思考一個更根本的問題:為什麼一個看似旨在幫助人們的系統,卻會變得如此低效且昂貴?
第一部分:佛利民的四種金錢——解構保險的失靈
要理解問題的根源,我們必須藉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·佛里曼(Milton Friedman)提出的、一個極其睿智的分析框架——「花錢的四種方式」。這個框架根據「花的是誰的錢」與「為誰花錢」,將所有消費行為劃分為四種類型:
第一種:花自己的錢,辦自己的事。
這是效率最高的模式。當你用自己的血汗錢為自己買東西時,你會極力追求物美價廉,力求將每一分錢的效用最大化。
第二種:花自己的錢,辦別人的事。
例如,你為朋友挑選生日禮物。此時,你仍然在乎價格(因為是花自己的錢),但可能不會像為自己買東西那樣,精確地在乎禮物的實用性與品質。
第三種:花別人的錢,辦自己的事。
例如,你用公司的經費報銷一頓午餐。此時,你只在乎午餐的品質,而對價格毫不在意,因為錢不是你出的。
第四種:花別人的錢,辦別人的事。
這是效率最低、也最浪費的模式。 你既不在乎花了多少錢(因為錢不是你的),也不在乎事情辦得好不好(因為事不是你的)。最佳的例子是政府支出,而政府支出佔GDP的比率會越來越高,造成我們生活品質的停滯。
CrowdHealth 之所以能夠找到那個極具成本效益的心臟手術方案,正是因為它的運作模式,還停留在佛里曼的第一種模式。它仍然是一個由創辦人親自運營的組織,創辦人將會員的資金視如己出,他有最強烈的動機,去為會員尋找最優質、最實惠的解決方案,因為這直接關係到他事業的成敗與信譽。
然而,傳統保險業之所以如此糟糕,正是因為它完美地落入了佛里曼的第四種、也是最糟糕的模式:一位「保險經理人」,用「所有保戶」的錢,花在「單一病患」身上。
在這個模型中,所有誘因都已錯置。那位保險經理人,即便知道自己家附近就有一家更便宜、品質同樣優良的醫院,他也幾乎沒有任何動機將病患轉介過去。相反地,最符合他個人利益、也最省事的作法,就是讓病患去當地最方便、但可能極其昂貴的醫院,然後讓病患自己去承擔那驚人的自付額。
這是因為在現行的保險體系中,經理人的薪酬和績效,往往不與「為保戶節省了多少錢」直接掛鉤,而是與其他因素(如處理的案件量、公司與特定醫療集團的合作協議)相關。這套系統從根本上,就缺乏節約成本的內在驅動力。
系統性的困境——從MRI到法規的枷鎖
這種由錯誤誘因導致的低效率,進一步被美國獨特的地理與制度環境所放大。
設備等病人:MRI的啟示
以昂貴的醫療設備核磁共振(MRI)為例,美國與台灣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運作模式:
台灣:人口密度高,醫療資源相對集中。MRI 的設備利用率極高,常態是「病人等設備」。雖然等待時間可能較長,但每一台設備的價值都被充分利用,分攤到每一次檢查上的固定成本也因此降低。
美國:地廣人稀,醫療資源分散。為了滿足各個社區的需求,許多地區醫院都不得不配置全套昂貴的設備,即便其使用頻率不高。其結果,便是「設備等病人」。大量的MRI在閒置中產生折舊,而這些高昂的閒置成本,最終都必須由為數不多的使用者來承擔。
這個例子揭示了,美國醫療費用的高昂,部分源於其人口分佈與醫療佈局之間的結構性矛盾。
法規的詛咒:大到不能倒的保險巨獸
要解決這個問題,直觀的想法是讓市場發揮作用,讓更靈活、更高效的小型醫療計畫(如CrowdHealth)去挑戰現有的低效模式。然而,現實是,美國的醫療保險產業,已被層層疊疊的複雜法規所綑綁,形成了一個由少數幾家「大到不能倒」的保險巨獸所壟斷的市場。
在現行體制下,一個大型保險公司的經營者,其首要目標已不再是「為客戶解決問題」,而是「確保公司符合所有法規,並有效管理這個超龐大的組織」。創新與效率,早已讓位於合規與維持現狀。
因此,要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的醫療問題,釜底抽薪之計在於減少不必要的法規,降低市場准入門檻,讓更多小型的、由創辦人直接面對客戶、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保險公司得以生存和競爭。唯有如此,才能將整個產業從佛利民的第四種模式,拉回到更接近第一種模式的軌道上。
一個艱難的取捨——品質與成本的再平衡
最後,我們必須面對一個更為根本的、甚至有些殘酷的現實:要大幅降低美國的醫療費用,或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,接受醫療品質的「下降」。
這裡的「下降」,並非指醫療技術的倒退,而是在微觀層面(對每一個獨立案件而言)放棄對「頂級便利性」的執著。正如心臟手術的例子所示,如果病患願意為了節省五萬美元而搭飛機去另一個城市,這在個體體驗上或許是一種「品質」的下降(需要旅行、離開熟悉環境),但在宏觀層面,卻是整個社會醫療資源效率的巨大提升。
如果能接受這種取捨,讓醫療資源更合理地根據人口密度進行配置,雖然微觀上某些地區的醫療品質會有所下降,但整體費用的巨幅減少,反而能讓更多原本被排斥在體系之外的人,享受到「足夠好」的醫療服務。
這是一個社會價值觀的選擇。而對於那些同時追求頂級品質和低廉價格的個人而言,解決方案或許也很簡單:搬到人口密度高的都市去。因為唯有在高密度的協作網絡中,專業化的分工與高效率的資源配置,才有可能同時實現這兩個看似矛盾的目標。